閱讀能力有5個階段,孩子的水平到了哪一級?

在閱讀中提升孩子的批判性思維
發展閱讀能力的五個階段
中國的孩子從小被教育“書中自有黃金屋,書中自有顏如玉”,讀書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高考是改變人命運的機會,現在看起來還是這樣。
考試的第一門是語文,語文和閱讀、寫作是分不開的。以前的閱讀與寫作主要是紙面上的,而現在也包括電子信息的閱讀。人們常以為,只要認得字就可以閱讀,其實不是這麼回事。
有一本書——《普魯斯特與烏賊魚》說,人不是天生就會閱讀的,閱讀是後天發展起來的能力。人的頭腦裡沒有專事閱讀的基因,需要借助一些已有的功能來發展出閱讀的能力。比如,人一生下來能夠辨別物體的大小、距離,人能夠學說話,而閱讀是綜合了這些天生能力的結果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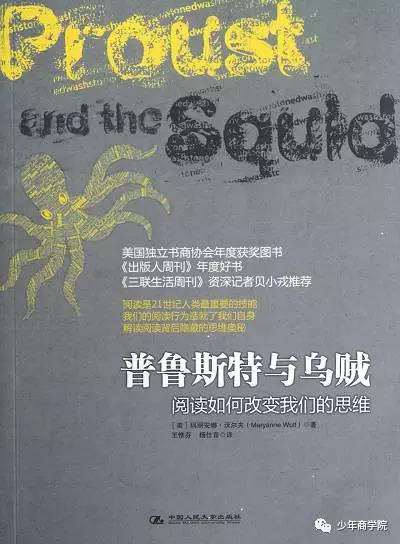
人類用了兩千年才發展出閱讀能力,一個孩子卻要用兩千天來發展這個能力。閱讀能力不是說發展就發展的,需要由低到高經歷五個階段:萌芽、初級、解碼、流暢、專家。
前兩個不說了,主要是說孩子念的一些啟蒙讀本。到了解碼級,就是比較正規的閱讀了。我們現在考的主要跟解碼級有關。
解碼是什麼呢?我們讀一篇文章,文字是編碼,要解碼就是要讀得 “懂”。但是文章不只是碼,閱讀也不只是解碼。所以到了流暢級,考察的是對文字之外意思的領會和解釋,比如說明喻、暗喻,這就是流暢閱讀需要的能力。更進一步,專家級是看孩子有沒有批判思維能力。
比如說,現在是冬天,樹葉掉了,氧氣減少,有人說需要一個氧氣枕頭。這句話,解碼、流暢都沒有問題,但是仔細一想不對。因為北半球是冬天的時候,南半球是夏天。而且,地球上的大部分氧氣並不來自樹木的光合作用,而是來自海洋。地球近赤道的地方並沒有冬夏變化,等等。
有很多的理由加在一起,最終你就會發現,一開始給你解碼的那個文本是有問題的,是虛假信息。這個例子算是可以用經驗和科學來識別的,但有些判斷是沒法用經驗識別的,如用意識形態對歷史發展的解釋。所以更加需要批判思維。

專家級的閱讀
解碼、流暢的閱讀都是技能性的,只有專家級閱讀是思考性的。
我們常常會通過文本訓練學生的閱讀能力。比如,讀莎士比亞的《凱撒大帝》,你先能夠解碼,讀懂文本,就很不錯了。那麼流暢級是什麼樣的呢?比如你讀這部劇,覺得這部劇可謂是莎士比亞所有劇中最理性的一部,給一些理由;然後你也可以找到一些非理性的東西,給一些理由;最後你把這些理性的東西和非理性的東西放在一起,讀出了文學的 “曖昧” 和人性的 “復雜性”。
接下來,就是為什麼要讀這部劇,可以從讀出什麼與今天有關的東西、對現在的生活有什麼意義?這就是專家級了。
布魯塔斯把凱撒殺死了,但是布魯塔斯並沒有得到政權,因為他被復仇的安東尼奧殺死了,最後得到權力的是什麼力也沒出的屋大維。我們把它放到現世政治中會發現,不少政治的 “謀殺” 都是這個規律,人算不如天算。比如蘇聯,赫魯曉夫把斯大林拉下神壇,但赫魯曉夫並沒有成為真正的贏家,因為他犯下了背叛的罪行。而下面恢復秩序的是勃列日涅夫。
如果把戲和現實聯系到一起,就是超過流暢閱讀的能力了。

停留在前2個階段,閱讀將失去意義
不同的教育方式都在培養不同的閱讀能力。比如上個世紀 50 年代的時候有掃盲運動,培養人看報、聽廣播,為的是便於接受官方的宣傳。這也是所謂 “學習領會” 的能力。
而文革以後曾講的 “讀書無禁區”,則是提倡獨立思考的能力。但學生進行流暢級以上的閱讀的機會是不多的,因為不是經常讀文史哲作品——比如,文學作品是很豐富的,有形成想法和訓練思維的能力,但是,讀文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
比如理工科的人,整天要做實驗研究,沒有時間;而外文系的,也要花很多時間在背單詞、學習語法之類的技能訓練上面。所以就算在大學,也很少有人有時間去讀文學。就算在文學系,也要看時運,看念的具體是什麼。
我原來也念過中文系,待了兩個月就走路了。那個時候文革剛結束,我們念的是《龍江頌》,或者郭小川的《團泊窪的秋天》,這些文革遺留下來的東西。它們的閱讀是有固定模式和正確解答的。
所以,要訓練批判思維,就要選擇合適的閱讀文本,要講究閱讀方法。
比如剛進來的學生,給他讀馬基雅維利的《君主論》,他能讀懂就不錯了。接下來就要給他講,那個時代的作家喜歡用什麼修辭手法,去分析這些修辭的文學性。
再接下來,就要引入一些政治學的概念,讓他們進行批判閱讀。比如馬基雅維利提到,統治有兩種手段,一個是用恐懼,一個是用愛,前者比較有效。讀的時候就要想:有沒有道理?恐懼可能有效,但道義上對不對?這些就是批判思考了。
所以說,我們不能停留在解碼和流暢這兩個階段,不然閱讀還有什麼意義呢?我們不是今天沒有事情干,才在那裡讀本《馬基雅維利》,我們讀是為了有目的地思考,而思考是有不同層次的。
我們現在處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,但信息和知識是完全不同的。不僅信息和知識不一樣,知識和智識也不一樣。比如說,文藝復興前期的知識指的就是記住古代的事情,記得越多就越有知識。這就好比冷兵器時代,你力氣大,戰斗力自然強。那個時候的知識是不需要甄別的。所有古代傳下來的知識,都是值得保留的。
到了 16 世紀,開始變了。蒙田出現了,知識觀在他那裡發生了變化。蒙田是非常有名的散文家,散文是 essay,essay 就是 try out 的意思。什麼是 try out?那就是把 “我” 放在知識的中心,對 “我” 有用的搜集起來,這個時候就有一個 “知識者” 了。蒙田的散文,都是“我怎樣”。這個時候,他就變成一個知識的處理者了。
我們現在需要記那麼多東西嗎?根本不需要,一上網就可以很容易搜索到的。但是記憶不是沒用了。就像意大利作家翁貝托·艾柯說的,你現在不需要走路去上班,但是你走路還是可以鍛煉身體。
記憶訓練至關重要
不是說有了電腦就不需要記憶了,還是需要,因為這是我們人類智識中重要的部分。念一本書需要短期記憶,要是念了後面的忘了前面的,還怎麼把它們串起來,融會貫通?念一本書,過了許久之後,念另外一本書時,聯想起以前念過的那一本,重新有所領會,這就是閱讀比較長期的記憶。
所以我們還是需要記憶。記憶力從哪裡來?就要訓練。文藝復興時期的時候,這麼多東西要記,怎麼辦?那個時候開始有 “記筆記” 這一回事,但不叫 notebook,叫 commonplace book。什麼意思?
比如一個書裡,描寫衣服的,描寫人的,分解以後記在筆記裡,需要用的時候拿出來組裝。要寫文章了,要描寫天氣,就去描寫天氣的筆記裡找,或者已經記得裡面記下的,諸如此類。
記憶對知識是非常重要的。埃及神話中說,書寫是由 Theut(希臘神話中叫 Hermes)發明的,他跟法老說,我找到一個很好的工具,來代替我們很不可靠、很脆弱的記憶,從此人們不需要靠記憶了,他們可以把東西寫下來。
法老一點也不興奮,他說,記憶是神給我們的能力,你現在用外在的力量來代替人內在的力量,使得人的靈性減弱了。書寫給了人用知識的假象來冒充知識的機會。我們寫的東西未必是我們真正懂的東西。博士論文、碩士論文,有的就是拾人牙慧,這是知識嗎?
寫跟想不是一回事。但是在教學的過程中,要盡量讓這兩種功能一致起來,要鼓勵學生寫他們理解的東西,要充分理解了,弄通了再寫,要說真話,清楚地把真話形成文字。想不清楚,就一定寫不清楚。不是說要寫得很華彩,用修辭代替說理就可以的,或者用個微博,發個一百多個字的警句格言,全是結論沒有過程,搞得跟維特根斯坦似的。
孩子寫文章,練過渡最重要
很多人的閱讀是消遣性的,用閱讀來放松自己。有人認為,閱讀可以使人跟別人不一樣,變得更有見識或更聰明;還有人覺得閱讀可以提高審美情趣或修養,有閱讀經驗的人比沒有的更能欣賞好的作品。閱讀沒有單一的目的。
這個其實和寫作是一樣的。我舉個例子,我認識一個老先生,是基督徒,寫了一本書送給我,跟我說:“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,受到了上帝的很多恩惠,因為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,發現了很多東西,是上帝給我的。”
其實,你寫作的時候,你是帶著目的去的,會發現很多以前不太注意的東西,這個是思考帶給人的更大的關注范圍和能力。這就是為什麼寫得多的人知道的越來越多,因為他會對越來越多的東西發生興趣。
如果對足夠多的東西發生興趣,那麼不光寫作的可能多了,而且有了一個把這些東西串聯起來的可能。

我媽老問我,你老是在寫,有沒有寫完的一天?我說不會的,越寫越多。寫作是個非常奇妙的東西,是個發現的過程。當然,寫不是說有個想法就完了,寫是要成文的,有結構的,而成文的能力也是在寫的過程中獲得和增強的。
我最近在給一報刊寫托尼·朱特的遺著《思慮 20 世紀》的書評。托尼·朱特跟我有相似的地方,或者說他讓我想到了自己與他相似的地方。他原來是個歷史學家,是個學院裡的寫作者,一個很偶然的機會開始受邀給紐約書評寫評論,起初不會寫,寫寫就會了。我開始也是走學院路線的,這個報刊找我寫評論,我推了好多次。我推辭,一個是不願意,另一個是我不會。
但是逼上梁山,慢慢地就會了。現在我覺得這種公共寫作對我太有用了,因為這使得我必須面對普通的讀者。給報刊寫文章,讀者都是有知識的,必須簡略一些,但不能太簡單。
寫到的問題是具體的,但同時也要能提出一般性的看法。一篇評論要有個由頭,但是就事論事是沒有意義的,後面一定要介紹一種理論、或者看法,或者某種知識。托克維爾的文章極有閱讀價值,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具體討論時,不斷在提出有意義的一般性觀點。
我的父親文章寫得很好,他不給我講文章,只給我改文章。我從他的改動裡悟出很多道理。比如說,文章最重要的是過渡,從一個想法到另一個想法要很流暢。好的作者有一個想法,不會一兩句話就過去,一定會在這個想法上停留足夠長的時間,形成一個段落,一個比較完整的思想。
從一個思想到另一個思想,中間一定要有過渡,這個過渡是你創造出來的。文章本來就是創作的,不會是自然的。所以很多人等待自然的過渡,可能永遠等不到。
我們在教學生作文的時候,不是叫他們寫 research paper,而是教 “I search paper”。比如要學生寫一篇波士頓河流污染的文章,首先要對這個問題感興趣,然後就寫,寫到知識窮盡的時候,這是第一步。
在這個過程會有很多想知道的東西,比如 100 年前河水是怎樣的,50 年前河水是怎樣的。不寫就不會產生想法。這個時候就會去找想要的知識,一次不夠,再寫,再搜索。
我們不會叫學生找幾本書,幾篇文章先研究一下再寫,以期下筆如有神或一氣呵成,這樣會把學生教傻的。

人文教育不等於知識拼盤
培養閱讀能力一定要有操作性。從教育的角度來看,一定要在具體的場景下開展訓練,超出這個就是空談。
每個人都不一樣,但是有些是基本的能力,每個學生念大學都必須有的,我們可以設置這樣的課程。這就是人文教育了。人文教育就是讀寫教育,聽起來輕飄飄,甚至老生常談,但其實不那麼簡單。
在我的學校,六門課是學生必選的,不管是理科生還是文科生。這些課叫基礎課,2門是寫作,4門是閱讀。我們在這幾門課上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、批判寫作以及說理等基本的技能。這幾門課是沒有主題的,不是 subject courses。
而通識教育就不一樣了。現在中國是什麼情況呢?基本上都是知識拼盤。比如數學系的,要選幾門英文系或人文、社會科學系的課。以此代替人文教育,是自己哄自己。
有些學校,英文系教浪漫主義文學的老師,教別的系的人還是教浪漫主義文學,對人文教育並無實際作用。這門課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批判思考能力呢?這是個很大的問題。
用通識教育代替人文教育,這沒什麼用處,很多大學的老師都跟我說,我們都明白你什麼意思,但是現在的體制下只能這樣。我認為,如果不把人文教育與通識教育加以區分的話,就不能設置符合人文教育自己教育目的的課程。
美國現在的教育觀念中有課程(curriculum)和教育課程(educational curriculum)的區別。前者是寫一個教學提綱(syllabus) 給學生,後者是一個總的目標,一些基本的東西,比如培養民主社會的公民或者人文教育的批判思維,是教育課程的目標。
但是現在中國做不到。有一次開會,一位上海的大學老師跟我聊到人文教育課的事情,我問她課堂上有多少學生?她說有一百多人。那怎麼教呢?怎麼討論呢?
這也許還不是最困難的,任何教育的最大困難都是教師。羅馬時期,教師的好壞對學生的影響不是一點點。學生跟老師學是要付學費的。學費怎麼付呢?教師會問學生,你以前學過沒有啊?
學生說學過一點。照理說學費應該便宜一點吧?不,學費雙倍。什麼道理?如果碰到的是差勁老師,學了不好的東西,還得把那些東西去掉,這樣後面的教師就要花雙倍的功夫在你身上。
現在碰到對人文教育力不從心的老師是常態。我很理解,他們自己都沒有接受過人文教育,他們怎麼知道人文教育怎麼教啊?
教育是個傳承的問題,而且教育是帶有制度記憶的,一代代傳下來的。制度性記憶很重要,形成了一個傳統,而且有積累,越來越豐富。

人文教育的課堂,討論為王
有經驗的老師和沒經驗的人文教育老師是完全不一樣的。不是說給學生布置一些閱讀文本就可以完事的。人文教育的重點在與學生與學生,學生與老師之間的討論和說理交談,而這是需要引導和訓練的,且每堂課上都會出現不同的情況,需要老師隨時與學生互動。
比如我們學校,一共也就 2000 個學生,一年差不多 500 個新學生,這 500 個學生要開大約 30 個班,那就需要 30 個老師。不可能找 30 個教古希臘文學和哲學的老師同時來教。
這就涉及到課堂上的教學具體要求:在人文教育的課堂裡,老師不是去傳授關於古希臘的專門知識,他是去引導課堂討論的,重點只是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。
當然,每個老師的能力不一樣,對學生的啟發程度當然也不一樣。比如讀歐幾裡得的幾何學,點、線、面和那些幾何公理,學生們中學都學過。老師就可以告訴他們,歐幾裡得幾何學的特點是用文字來表述的,用文字形成一個概念的體系,這與埃及幾何只用圖像來表示是完全不一樣的。
歐幾裡得裡面,所有的推論都是從一個點的概念,也就是定義出發的。點的定義是什麼?點只有位置,不佔空間。所以你把點畫在黑板上,那就不是點了,因為它佔了空間。所以真正的點只能存在在頭腦裡,這就是柏拉圖的想法。
那麼就要問了,我們看到的任何點都不是真正的點,但作為人可以理解點的概念,這是為什麼?可能是因為上帝給了人這個能力,也可能說是人有某種學習的基因。這樣的討論會讓學生對人更感興趣,也有新的認識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