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代少女「百合」,是如何在日本起源的?

近年來,有著百合標籤的ACG作品越來越多。僅是2020年秋季動畫,就有《突擊莉莉》、《安達與島村》、《Love Live!虹咲學園學園偶像同好會》等受矚目的作品。
就如前幾年也有《終將成為你》、《小林家的龍女僕》等等,大部分動畫觀眾耳熟能詳的佳作。
而在觀眾熱切討論之餘,一個從「百合」一詞出現以來就被不斷爭議的話題也逐漸在輿論中擴散開:到底什麼是百合?百合和lesbian有什麼區別?
再來什麼樣的作品才算百合作品——美少女和美少女之間產生糾葛就夠了嗎?
以《突擊莉莉》來說,它展現了一個「魔法少女打怪獸順道在校園裡卿卿我我」的經典開局,但具體到鏡頭表現上,又大量聚焦在大腿與歐O,怎麼看都有著打著魔法少女旗號在賣福利、回應男性凝視之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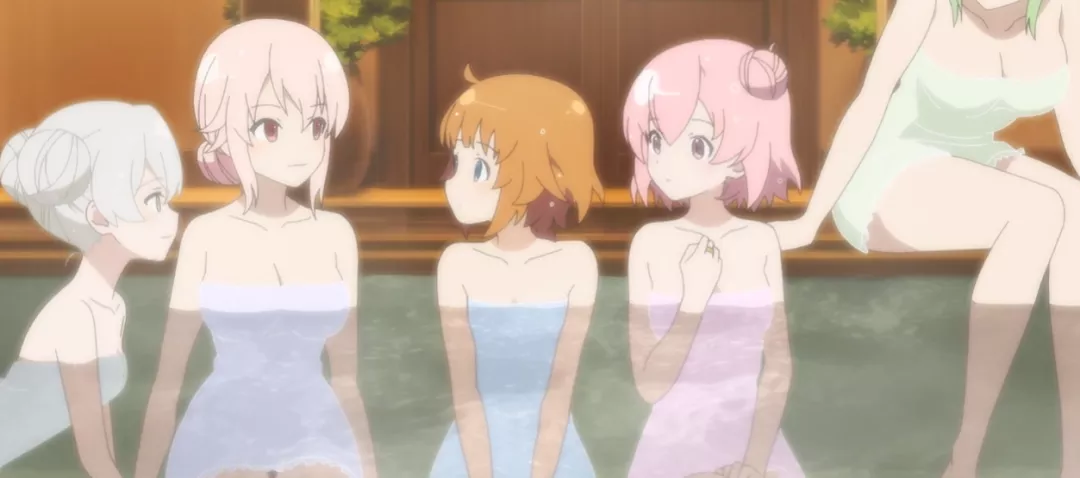
但是呢,這部動畫偏偏又採用了極為正統的「校園姐妹情」套路,和被視為百合熱潮先驅的《瑪莉亞的凝望》如出一轍。
那這種明顯是針對男性觀眾的動畫,算不算百合動漫作品呢?
實際上,至少從二十年前開始,日本的百合愛好者們就已經開始探討這些問題,但到今日其實也沒有一個能令所有人信服的結論。
對於這種定義概念類的問題,我們不妨追根溯源,看看我們現在稱之為百合的文化,到底是怎麼在近代日本的女校中誕生,接著又傳播到大眾文化中的。
S文化源起
《人生苦短,戀愛吧少女 大正戀愛事件薄》插畫繪/マツオヒロミ
現在人們常說的「百合」一詞,其實不完全等於lesbian。百合這個詞來源於上世紀1970年代的「百合族」,而其深層核心可以再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的日本。
在明治時期以前,女性被認為只要乖乖待在家裡就好,因此通常只會接受識字級別的教育。而進入明治時期後對女性的教育逐漸普及,應運而生的,就是各間女子學校。
1870年舶來的教會女校,與1882年東京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女高的建立,象徵著日本女性教育黎明期的到來;而真正的轉折點,則是1899年《高等女學校令》的實施。
這條法令規定,各個縣至少要建立一所高等女學校,因此僅兩年間,就將原本不足一萬的女學生數量擴到了兩萬多。
直到大正末年,已有近三十萬女學生在高等女校就讀,大量高等女校的成立,就是百合文化的社會背景土壤。
當年的日本女校
彼時的高等女學校並不設立國高中部,而是從12、13歲開始的五年制學校。對於正處於青春期的少女們而言,高等女校並不僅僅是學校,同時也是被指定結婚前的避難所,是「沒有丈夫的公主們的國度」。
這五年,事實上也是少女們一生中,幾乎唯一可以自由戀愛的時節。憧憬戀愛的年紀和只有女性的環境,畢業後就會嫁人、喪失自由的現實,或多或少都推了這些女孩子一把。
當時,對羞於當面表達感情的女孩子們而言,與朋友間頻繁的書信交流成了校園生活的重要部分。
這些充斥著激烈情感的信件,不僅是少女們情感的宣洩口,也是與友人維繫、加深情感紐帶的重要方式。也是在這種背景下,名為「S」的文化出現了。
至於什麼是S文化——這裡不妨引用川端康成與中裡恆子合著的著名S文學《少女的港灣》中的段落:
「基督教會的女子學校與官立的女子學校相比,學生之間的人情可謂更加細膩微妙。她們用各式各樣的愛稱來彼此稱呼,而高年級學生與低年級學生之間的交往更是熱情奔放……」
「所謂的『S』,就是Sister(姐妹)的省略……一旦某個高年級學生與某個低年級學生變得要好了,那大家就會這麼稱呼她們,並鬧得滿城風雨。」
「說起『要好』的話,和每個人都要好總可以吧。」
「哎呀,才不是那麼一回事呢。彼此得特別地喜歡對方,互贈禮物甚麼的……」

《少女的港灣》 繪/中原淳一
在1950年發行的《隱語詞典》,更是簡單明脆地直接將S定義為「在女學生之間的,高年級學生與低年級的美少女近似戀情般的關係。」
S的同義隱語在當時也有不少,並根據學校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稱呼。如1910年10月的雜誌《紫》記載的「瞳」(お目)一詞:
「上級的女學生看到了清純可愛的新生……會對朋友說:新入學的大家都很可愛,想去親眼看看呢(お目にしたい)……若是心儀的新生少女還尚未名花有主,便會將意味深長的紫色,或包含思緒的紅色緞帶熱切地交給那人;彼此會用『我的瞳』(お目さん)這一隱語來稱呼對方」
這種充滿儀式性的饋贈,是這種高低年級一對一的S文化的重要環節,在《少女的港灣》中,是花朵與回信;在二十年前的《瑪莉亞的凝望》中,是念珠。
在當時深受日本影響以至於同樣發展出S文化的韓國,姐妹間甚至會互送戒指。在饋贈物品之餘,姐妹們還有交換書信、一起上下學、外出購物、一併學習、穿一樣的衣服、梳一樣的髮型等親密行為。
而重中之重的書信,則因為飽含了愛慕、崇拜、憧憬等情感,而變得無比熾烈。
在當時的少女雜誌《少女畫報》中,作為讀者投稿一欄的「薔薇之所」,就收到了很多少女寫給其他女孩情書般的信。
「你什麼都不知道。我的嘆息。我的孤單。我的淚水。我的信。所有的所有都在等著你呢……我愛著你哦。你的眼睛為什麼那麼漂亮啊。你的眼睛為什麼就那麼攫住我的心呢……我的胸口快被撕裂了啊。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啊。(投稿者)正木麻美《寫不出來的事》」
當時要給S對象的信,若是羞於當面給予,便多半會投到對方的鞋箱中——《女學生手帖》
另一篇充滿少女心緒的信,其糾結與激烈的情感,更是跨越百年而毫不褪色。
「姐姐大人!我的姐姐大人啊!!請原諒我。至少請允許我在心裡這樣呼喚。那時我到底怎麼了?……一分鐘也忘不了姐姐大人。我是幸福的。和去世的母親一般寵愛我的姐姐大人。
我是個因為早晚都和你黏在一起,而無法將想傳達給你的事說出口的膽小鬼。在房間裡只有我們二人的時候,什麼話都說不出口的我,只能聽到自己小小胸口裡那瘋狂的心跳聲。也許不在同一個寢室才會更幸福嗎?
那是星期三的放學後。獨自回到房間的我,突然留意到旁邊桌子上的日記。姐姐大人,請原諒我。雖然知道不好,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姐姐大人的心聲。
『與所愛之人同處一室的喜悅與悲傷——快要溢出的血潮在胸口燃燒。將一切的一切都壓抑著的自己,是多麼壞心眼啊。』
這行筆跡,在那一瞬,在我胸口留下了刻痕。
這些話就這樣被我盜走……這樣真的好嗎?這種不安從心底裡升起。我當即就向姐姐大人寫了信。再也忍不住了啊。只是因為是個膽小鬼,那張粉色的信紙也被煎熬的心給燒掉了。
但是今天,我下定了決心。
——請原諒任性的我的一切吧——
寫於星期六的夜」
少女畫報繪/高畠華宵
刊載瞭如此多少女心緒的《少女畫報》,曾在1926年對S文化進行了一次令人忍俊不禁的定義:S,Sister的首字母。姐姐妹妹的意思。主要是用語稱呼妹妹。以下略。
……到底是略掉了什麼,真是讓人在意啊。
少女雜誌與《花物語》
如此浪漫的現實,不僅是文學的土壤,也是被文學反哺的產物。在沒有網路與電視的年代,如上述《少女畫報》一般面向少女的雜誌,作為當年少女們的主要娛樂手段之一而廣為流傳。
從1902年,第一本少女雜誌《少女界》創刊之後,《少女世界》、《少女之友》、《少女俱樂部》等雜誌也紛紛創立。
也就是在1916年的《少女畫報》上,吉屋信子開始連載被視為現代百合文學開端的《花物語》。在此後的十年裡,吉屋信子以《鈴蘭》為開端,以《曼珠沙華》為終結,斷斷續續描繪了52篇少女與少女們的故事,都是以花為名,鮮少有幸福圓滿的結局。
在《花物語》中,幾乎所有篇章都著筆於「邂逅-離別」這種模式——從相處幾年後的畢業、展開新的人生乃至失蹤與死別,到偶然一見鍾情,在短暫地相遇後患上相思病等等。
1916年,《花物語》第一次登上《少女畫報》
1926年,十年後的《少女畫報》上琳瑯滿目的花小說,與展示少女給少女信件的欄目「薔薇之所」
在吉屋信子的筆下,登場的少女們的關係不僅僅是前後輩,同學、教師,偶遇的少女,都可以是故事的主角。
地點也從學校與宿舍,到了故鄉和家庭,《白萩》、《水仙》、《蘭》三篇,則是乾脆迷了路後偶遇另一位主角,也就是所謂「不可思議的相遇」。
關於角色間的糾葛,吉屋信子當然也不會放過三角戀。如《麝香豌豆》中,病弱卻活潑的美少女新生綾子,被綾子傾慕的虔誠牧師的女兒佐伯,以及作為佐伯好友卻偷偷在圖書室和綾子見面、充滿罪惡感的主角真弓,這三個人之間構成了微妙的關係。
在一次失敗的舍監抵抗運動後,舍監以“虔誠的基督教女孩不會撒謊”為由,逼問虔誠的佐伯抵抗事件的始作俑者;而知道罪人之一是綾子的佐伯最終選擇了違背信仰,撒謊說自己忘掉了。
知曉這一切的真弓選擇了主動退出,在信裡告訴綾子她覺得違背了信仰的佐伯才更適合綾子後,逐漸開始避開綾子。到了第二學期的冬季,病弱的綾子去世了。在聽合唱的讚美詩時,真弓和佐伯依偎在一起哭了起來。來年的春天,兩個人一起掃墓後,真弓去了專科學校,佐伯則選擇了神學院,兩個人就此踏上了各自的旅程。
作為花物語晚期作品的《麝香豌豆》不僅描述了三角戀愛,同樣也彰顯著吉屋信子在連載十年後對百合文化的思考,這種對於規制的叛逆,實際上也貫穿了整個百合與S文化。
與小說作者同樣受追捧的,還有將少女們描繪出來,常出沒於少女雜誌之上的「抒情畫」畫師。
如同今天的追星一般,在當時的少女中也分為「華宵黨」、「虹兒黨」等畫師粉絲派別。
繪/蕗谷虹兒
用花來抗拒這個世界:S文化的社會影響
吉屋信子並非是當時第一個筆鋒流轉於戀愛病與真實病症的作家,在花物語連載前,1911年5月的《東京朝日新聞》就報導了「女學生間的戀愛流行病」:
「她們臉頰上的緋紅並非猩紅熱,而是一種流行的戀愛病……雖然之前就有洋化之風與虛榮心盛行,但這個同性間的戀愛病,是會讓女學生品性墮落的可怕精神疾患……十年前就有徵兆,近兩三年有來愈演愈烈之勢……染上此病的女學生,大多是有看那些雜誌、小說……」
逃往小說的世界似乎是必然的,現實世界對於少女們的桎梏一直都在。不得不聽從父母的安排,與定好的男人結婚,生孩子——一切都讓「結婚」這個詞幾乎等同於不含什麼愛意的、簡單的肉體關係。
而作為對比的,便是女學生之間幾近純粹,又在彼此廝磨中不斷精神化、理想化、乃至浪漫化的聯繫。
壓迫的現實,百合文學的百花齊放,哪怕獲得了愛慕的姐姐,或是可愛的妹妹也只有短短五年的自由……這些要素一併促成的「空想戀愛流行病」,在一些女學生看來是簡直再正常不過的事情。
同年10月《東京朝日新聞》就記載了來自女學生理直氣壯的反駁:
「認為同性之間的愛是不可思議的狼狽的教育者們啊,灌輸『男人都是巧舌如簧的嘴臉,男人給的信都是惡魔的勸誘』的人不就是你們嗎?被灌輸這種東西,去愛其他女孩子,不是再正常不過——不如說若是鮮有同性之愛才是怪事吧?」
在這樣的爭論之間,1911年的7月21日發生了一件事。時年二十(約畢業兩三年)的曾根定子在家裡,因為被定了親事甚為消沉。她被父親一再告誡,她與女校時代就無比親密的朋友岡村玉江(同為二十歲)的「友誼」有些越界了。
她從家裡溜了出來。同日,岡村玉江也同樣溜出家門。兩個人從東京的飯田橋經過直江津,最後抵達了新潟的糸魚川。26日,二人在糸魚川的親不知海邊,雙雙殉情。
這次殉情事件,像是往本就熾熱的油鍋中灑了水一般,一時以記者和教育家為中心,「女學生間的親密交友是否過於危險」這類話題可說無比火熱。
幾個月後,在譴責過於激烈的情感後,《婦女新聞》發表了一條和事佬般的評論:女學生的熱情決不能扼殺。最重要的是,要在適當的時候引導它燃燒。
最終,尋求解決方案無果的社會與校方讓了步:不扼殺,放任少女們在校園裡燃燒。
只要畢業後可以結束這種關係,那麼對於校園內女學生間的過度親密,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於是並未遭到過度壓迫的百合文化與百合文學,依舊在蓬勃發展。
只是這種放任,更像是一種憐憫般的妥協。
1930年左右,日本大量的女學生殉情事件發生;甚至這種風氣也飄到了S文化同樣盛行的韓國,因為S的對象結婚而留下遺書「好想姐姐給我一個窒息的吻」然後自盡的事件也發生過數次。
1931年4月8日上午11點,那天是個星期三,一個叫金永珠的韓國女孩來到了女校時期的朋友洪玉林的家。
下午4點,這兩個穿著時尚的二十多歲姑娘在永登浦站下了車,在向一個小孩子問了仁川的方向後,她們笑嘻嘻地給了小孩十枚硬幣作為獎勵。
之後她們牽著手沿著鐵軌經過兩旁盛開的杜鵑花,踏著尚未化開的積雪走了四十多分鐘。在下午4時45分,她們抱在一起,向從仁川開往首爾的428號列車衝了過去。
「我在事發的前一天晚上發現了遺囑……」洪玉林的母親回憶,「但真的沒想到會發生這種事。因為她們離開家時是笑著的。」
社會對兩個家境寬裕的少女死亡當然是震驚且不解的——直到發現兩個人的關係,與二人不幸的婚姻。
「她那時被困在房間裡,只是一味地讀著日本的愛情故事。」
「婚姻奪走了她的一切。」
改編金洪二人殉情事件的韓國戲劇
儘管在如今看來,實際存在的S文化並不如文學界那麼「純粹地前後輩一對一」,也擴散到了同級生或是師生間,但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世,有一個標準是非常鮮明的:
S不同於純粹的女同,它更趨近於女學生與喜歡的人之間一種純粹的精神紐帶,與個人的性別取向無關。換句話說,是只有女性的柏拉圖式戀情,當時社會對S甚至是殉情的容忍,也多出於此。
純潔的女學生進行「戀愛的預行練習」、「異性戀的前階段」、「青春期暫時性的感情」……諸如此類的說法在當時很多,若是女學生間逾越了只限精神的紅線,也會被立刻打上「異常」、「病態」等標籤。
身為女同的吉屋信子也是如此,即便她的百合小說備受讚譽,當她寫出較露骨的《黑薔薇》等作品時,抨擊的浪潮也如約而至。
由此,在S的關係中只存在精神的柏拉圖模式,算是女學生們與社會的默契。
如今回溯,百年前的社會對於感情的區分可說相當傲慢,它使用了「好感度一般是友情,好感度高了是愛情」這種粗暴的單向量劃分,這對於當年的女學生們也幾乎沒什麼意義。
倒不如說,當時的少女憑藉她們懵懂而熾烈的情感,以S之名摸索出了只屬於她們與姐妹間,各式各樣曖昧而微妙的情感關係。
而這種微妙的關係,也同樣被《瑪莉亞的凝望》等作品繼承,作者今野在採訪中表示:「我的作品被說成是『戀愛』的話有點不對……也不能單純地說是『友情和尊敬』。如果說是不同於戀愛的百合的話,那麼百合的意思會相當複雜。她們(指《瑪莉亞的凝望》的角色)之間的關係,是很模糊的。」
或許也正如《丸子與銀河龍》中阿爾可與丸子的問答:
——既不是戀、也不是愛,究竟是什麼呢?這種溫暖的感情,也不是家族,那是友情嗎?
——那一定,什麼都不是吧。還尚未化作詞彙,沒有誕生的感情吧。

人生苦短,莫被詞彙束縛了啊少女 圖源/《丸子與銀河龍》
